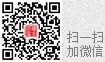日本社会企业
一、政策背景
日本社会企业政策出台背景与我国相似的是,在日本首先关注井积极推动社会企业实践和发展的力量亦来自民间社会。进人21世纪后,日本民间机构纷纷成立有关社会企业的研究会井组建相关支持机构,力图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然而,与我国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对社会新动向一直比较关注并能够及时回应。2007年9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牵头成立“社会化商业研究会”(‘注:“社会化商业”的英文表述为Social Bnsiness,等同于“社会企业”之意),其成员包括专家学者、非营利部门领导人以及企业界代表,同时邀请其他中央部委的有关负责人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该研究会成立后随即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企业制度展开详尽调查并于2008年4月发布《社会化商业研究会报告书》。
尔后,经济产业省委托三菱uFJ调查咨询股份制公司展开有关社会化商业的进一步调查,并于2010年2月发布《平成21年度地域经济产业化活性化对策调查报告书》(别名为“有关社会化商业的统计及其制度化探讨的调查报告书”)。同年10月,经济产业省再次牵头成立“社会化商业推进研究会”并于2011年3月发布《社会化商业推进研究会报告书》。正是根据这3部研究报告书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以经济产业省为核心的日本政府部门相继出台并实施一系列旨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直接性或间接性政策。
二、政策层级与架构
虽然日本政府从2007年起就已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企业法律制度展开调查,然而时至今日仍未出台有关社会企业的法律制度或认证制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日本现有法制框架中创设新的法律制度绝非易事,需要多方论证和各方协调,成本较高;二是通过改进和完善现有法人制度框架,能够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足够大的制度空间。宏观上,日本持续开展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为了更好地服务和管理社会企业的主要形态——NPO法人,日本的NPO法自1998年出台以后,以平均“两年一优化”的频率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修改,虽然制度的修订回应了社会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但也直接使社会企业的合规成本增加①。
(一)中央层级的社会企业政策
从2007年起,以经济产业省为核心的日本中央政府将社会企业视为“新型产业”,并从产业政策的高度实施各种支持政策。这些支持政策涉及社会认知度的普及、管理技术的援助、人才培养和开发、融资和筹资服务以及社会网络构建等内容。
(二)地方层级的社会企业政策
在地方自治制度架构下,日本地方政府拥有高度自治权,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自主灵活地实施有关社会企业的支持政策。截至目前,绝大多数的日本地方政府均实施了针对社会企业的培育扶持政策,其中包括政府补助、融资、认证、人才培养、人员派遣以及社会认知度普及等内容。
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的单一制国家,其政府机构分为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其中后两级政府在法律被称为“普通地方公共团体”(通称“地方自治体”),依法拥有自治立法权、自治行政权与自治财政权并负责实施团体自治和居民自治。在这种政治行政体制架构下,日本政府所实施的社会企业支持政策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法人制度,为社会企业家提供合法且多样的行动框架。
三、社会企业范围
2012年底安倍政府上台后,致力于推动以大型企业为主要对象的“安倍经济学”,从而直接导致之前作为中小型企业和地域经济产业政策一环的社会企业政策陷人停滞状态在遭到来自市民社会的批判后,安倍政府近期开始重视社会企业政策。2015年5月,日本内阁府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企业活动规模的调查报告书》、试图在全面把握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在这份报告书中,日本内阁府放弃“社会化商业”的提法,转而采用“社会企业”一词并提出社会企业所需满足的7大要件:①通过商业手段改善或解决社会问题;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③利润主要用于事业的再投资,而非将之全部分配给出资人或股东;④分配给出资人或股东的利润低厂全部利润的50%;50事业性收人额占组织整体收人的50%以上;⑥事业性收人中来自公共保险(医疗或护理保险等)的收人低于50%;⑦事业性收人中来自政府委托事业的收人低于50%。此外,该份报告通过抽样问卷调查等方式估算出日本社会企业的整体规模,即截至2014年底,日本社会企业共有20.5万家,雇用人员总数达到577.6万人,其附加产值高达16万亿日元(占到日本GAP的3.3%)。换言之,近年来日本社会企业获得长足发展,其政策效果较为显著。
正如美国凯琳所观察到的,日本社会企业的合法形式表现为非营利法人和企业相混合的模式。换言之,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决定了日本社会企业的发展可能性及可行方向②。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最终可归结为日本特有的“法人制度”,因为它赋予日本社会企业合法且高效的“行动框架”。根据日本官方所披露的,日本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包括中小企业、NPO法人、一般社团/财团法人以及公益社团/财团法人。为此,以下就这四种组织形态的法人制度进行简要分析。
1)中小企业法人制度。1999年,日本政府修订《中小企业基本法》并将中小企业定位为“在不同社会领域开展特色事业,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并为个人能力的发挥创造机会,从而奠定日本经济基础的企业形态”。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根据该法规定,日本中小企业可获得以下支援:第一,中小企业支援中心和地域力连携据点(商工会、商工会议所以及公社等)提供的经营支援,包括窗口咨询、专家派遣、研讨会参与、经营战略和商业方案策定、资金筹集、财务管理、技术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支援;第二,创业和风险投资国民论坛、创业塾、地方政府举办的各种研讨会以及中小企业大学提供的人才培养支援;第三,中小企业综合展、风险投资高峰会以及地方政府资源配置活动等提供的市场开拓支援;第四,商店街、本地产业、农商工连携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等提供的直接资金援助;第五,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信用保证制度提供的融资援助;第六,中小企业轻减税率制度、人才投资减税制度以及天使投资税收优惠制度提供的税收减免优惠③。
2)NPO法人制度。1998年,日本政府出台《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通称NPO法),采取认证原则(即申请组织所提交的材料只需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即可获得认证)以降低法人注册门槛,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干涉法人的日常运作。目前,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通称NPO法人)虽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的20个特定非营利活动领域开展公益活动,然而由于这些活动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从而在实质上推动NPO法人在日本社会各领域开展公益活动。此外,在NPO法实施的前3年间,NPO法人仅享有与非法人型NPO相同的税收优惠,即其会费收入、捐赠收入以及政府补助收入等可被纳入法人税和法人居民税的非课税对象。2001年,日本政府通过修订NPO法创设“认定NPO法人制度”。根据这项制度,凡是满足包括公众支持测试度基准在内的认定基准的NPO法人可享受以下税收优惠:首次,在法人税方面享受“视作捐赠免税”待遇,即营利事业的部分收入(最高为50%)可被视为内部转移捐赠并享受免税待遇;其次,市民或企业所提供的捐赠享受基于“税额控除”或“所得控除”的减税待遇;最后,因继承或遗赠而取得财产者所提供的捐赠不计入继承税计税范畴。另外,作为NPO法人的起步支援措施,日本政府从2012年4月起实施“暂认定制度”,即处于设立初期的NPO法人只需满足除公众支持测试度基准之外的认定基准,即可获得“暂认定NPO法人”资格,从而享受除遗产捐赠免税和视作捐赠免税之外的税收优惠待遇④。
3)一般社团/财团法人制度。一般社团/财团法人(统称“一般法人”)的制度特征在于法人享有极高的自由度。首先,法人注册手续简易,同时法人的事业目的和事业内容没有任何法律限制。换言之,在不违反其他法律的前提下,一般法人可从事任何不以营利为目的事业。当然,与营利法人不同,法律禁止一般法人进行利润分配。不过,这种利润分配禁止属于非完全性利润分配禁止,其原因在于:法律虽然禁止一般社团法人向其会员进行分红,但却未禁止其将利润或剩余财产分配给组织干部或会员之外的个人或组织。此外,法律允许一般法人通过权力机关的决议将组织剩余财产分配给会员或组织创始人。其次,将公权力的介入和干涉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通过法律规定以促使法人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概括而言,设立一般社团法人仅需2名会员,而设立一般财团法人只需筹集不低于300万日元的原始基金即可。之后,发起人只需将组织章程进行公证并提交至法务局进行法人登记后即可获得法人资格。由于一般法人在事业目的和事业内容方面拥有很高的自由度,故基本无法享受税收减免待遇。不过,那些满足税法规定的“彻底贯彻非营利性的法人之要件”或“以共益性活动为目的的法人之要件”的一般法人可被视为“非营利型法人”,从而享受诸如会费收入免税等若干税收优惠。而除此之外的一般法人(即税法上规定的“普通法人”)则与营利法人相同,其所有收入均需课税。
4)公益社团/财团法人制度。公益社团/财团法人(统称“公益法人”)是指满足公益认定基准并获得公益认定资格的一般法人。根据《关于公益社团/财团法人的认定等法律》(简称《公益认定法》)的规定,公益认定基准主要包括:以实施公益目的事业为主要目的、具备实施公益目的事业所需会计基础和技术能力、禁止在事业实施过程中向与法人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提供特殊利益、禁止在事业实施过程中通过捐赠等方式向营利团体或以谋求特定个人或特定团体之利益为宗旨的团体提供特殊利益、公益目的事业收入不超过实施该事业所需合理费用、公益目的事业所占比率超过50%以及闲置资产不超过法定限度额。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公益目的事业,是指《公益认定法》所列举的有助于增进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23项公益目的事业。一般而言,公益法人除了收益事业所得收入(营利性收入)之外的所有收入均可享受免税待遇。不过,《公益认定法》规定的收益事业并不等同于《法人税法实施令》所规定的收益事业。换言之,公益法人所实施的事业一旦被认定为《公益认定法》所列举的公益目的事业,那么既是属于《法人税法实施令》所规定的收益事业,也照样能享受免税待遇。此外,公益法人即使实施需要正常纳税的收益事业,如果将该事业所得收入用于公益目的事业支出,那么被转移支出的那部分收入(最高可达到100%)可被视为“公益目的事业财产”,从而享受免税待遇。此外,公益法人还能享受捐赠免税等各种税收优惠⑤。
简而言之,通过改革和完善现有法人制度,日本政府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了多种合法且高效的行动框架:如果青睐纯市场化运作模式,可以采取中小企业的组织形态;如果侧重通过动员志愿者力量以开展小规模的公益创业,可以选择NPO法人的组织形态;如果倾向完全自由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创业,可以注册为一般法人;如果有志于开展纯公益且信誉度较高的公益创业,可以选择公益法人的组织形态。
在社会企业概念传入东瀛之前,类似社会企业的实践活动已在日本得到推广和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开始出现肩负社会使命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或以促进民主参与为宗旨的市民事业(Civic Business)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重建社区以及激活地域活力,日本社区层面开始涌现大量的“社区事业”(Community Business)。根据日本官方的定义,社区事业将地域问题的解决以及挖掘和利用地域资源视为商机,以本地居民为行动主动,在激活地域活力和践行社会贡献活动的同时,努力实现事业的自律性和可持续性⑦。 进入21世纪,社会企业概念传入日本并在美国流派和欧洲流派的双重冲击下,日本学界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逐渐形成三大流派,即产品或服务经营收入学派、社会创新学派以及社会经济学派⑧。 换言之,日本学界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呈现百家争鸣之状态,迄今为止仍未形成统一认识。尽管如此,日本学界的研究仍对政府决策产生巨大影响。
日本社会企业主要致力于区域振兴及城市建设,促进地区发展,推动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的解决,属于区域课题解决类企业⑨。 活动领域主要包括:1)为激发城市活力,在城市建设、旅游观光、农业体验等领域进行人才培养和相关组织建设;2)为地方市民提供育儿支持和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3)为环境、健康及劳动就业等领域建设社会组织机构;4)为企业家培养、创业及经营提供相关支持。其中,与社区发展相关的前两项占总体的78.2%⑩。
四、主管部门
日本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扶持主要由内阁府和经济产业省推进。内阁府以实现“新公共”政策为目标,通过新公共支持项目与区域社会就业促进项目这两大项目来倡导社会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经济产业省委托日本社会企业发展研究会牵头,致力于推进社会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经营环境的改善,提供多样化的社会企业支持项目,确保“新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对于社会企业认证、法人资格认定与税收减免资格认定,第一,1998年出台NPO法(全称为《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并进行多次修订,将涉及NPO法人的行政事务全部下放到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尊重NPO法人的自治和自律,将法人资格的获取和税收减免资格的获取相分离,大幅度放宽税收减免条件,创设“视作捐赠制度”(即允许NPO法人将营利事业的部分收人以捐赠的形式算人公益事业所需经费,从而享受免税待遇)等等,允许并鼓励NPO法人通过开展营利项目获取收人并用于与组织宗旨相关的公益事业。第二,2006年推行公益法人制度改革并于2008年实施新公益法人制度。新公益法人制度采取与NPO法人制度相类似的“二级架构”,将法人资格的获取和税收减免资格的获取相分离,一般社团法人和一般财团法人(简称“一般法人”)的注册方式与公司法人无异,只需根据法律要求制定章程并递交公证处进行公证后,即可到法务局进行法人登记。一般法人没有行政主管部门,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可以从事任何领域的社会活动,享有极大自由。当然,一般法人想要获得税收减免资格,就必须执行彻底的非营利原则、并向第三方独立机构申请公益社团法人或公益财团法人的资格认定。根据内阁府发布的报告书显示,上述营利法人、NPO法人、一般社团法人、一般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公益财团法人,正是构成日本社会企业的主要组织形态⑪。
表1 社会事业法人方案的主要内容
| 制度 | 内容 |
|---|---|
认证及更新制 |
■ 实施认证制,每两年进行资格复审; ■ 资格复审若未通过,补充材料后亦未达到相应条件的,将取消社会事业法人认证资格。 |
发行非分红股份税额扣除 |
■ 持有社会事业法人股份的投资者,享有通常意义上的股东权利; ■ 股份不参与分红,但可以流通和转让,降低了筹资难度。 |
企业收入视为捐赠抵税 |
■ 投资者的出资可以抵扣税款。 |
法人税率 |
■ 盈利性收入【限50%】在税法上视为捐赠收入抵税。 ■ 税率与一般社会团体法人一样,均为30%,但其可以成为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对象。 |
剩余请求权 |
■ 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社会事业法人的债务,剩余财产归政府所有。 |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部,2010
政策支持内容
概括而言,日本社会企业政策主要涉及以下6个方面:
(1)创造并改善社会企业的筹资环境
建立捐赠渠道。例如:在当地企业中举办捐款募集说明会;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融资成功率;给予贷款补偿;建立有利于积累地方社会资本的组织机构,推动“社会创新”事业发展。
探索建立社会企业法人制度为扩大社会企业的融资渠道,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2010年内阁府提出“社会企业法人”的提案。目前日本有非营利组织约4万个,但经营规模在3000万日元以上的不到15个,由于这些组织的规模有限使其在面对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时的作用有限。而社会企业法人制度在设计上更加灵活:认证条件简单而开放,采取复审制度以提高社会企业的公信度;融资也更加便利,其与既有的非营利法人相比,对政府财政的依赖降低,实行的非分红股份、税款优惠、捐赠可以抵税、适用特别法人税率和余额请求权等方式在启动大规模非营利性福利事业时更方便。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推动各种地方金融机构以及国家金融机构向社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2)推动社会企业建立与培养社会企业发展所需人才
除了“新公共支援项目”,内阁部以推进社会企业的建立和人才培养为目标,2009年到2011年,共计投入70亿日元展开“区域社会就业促进项目”。内阁部以招标的方式,从社会企业中选定12类组织,以增加就业和提升社会企业的人才质量为内容,开展以下两项工作:第一,向社会企业家提供孵化支持。以每人300万日元为限,被选中的社会企业家将获得一笔“创业资助金;第二,为初创社会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在地区社会企业中工作六周以上的人员,可以获得内阁部发放的10万日元月薪补助。
中央政府还通过举办各种培训项目以及与大学机构等的合作,培养和开发社会企业发展所需人才⑫。
(3)支援社会企业开展相关项目
2009年,内阁府制定了作为日本未来发展的重要经济政策,实施区域社会就业促进项目(项目期三年,项目费70亿日元)。该项目以促进就业为目标,其特点是政府不再为创业者直接提供资金,而是将部分资金分配权交给民间,实现了政府的分权化。由内阁府进行公募,经过外部专家遴选,挑选出12个法人主体(非营利组织的民间事业者、地方自治体和协会联盟等)对“社会创业孵化项目”和“社会企业人才创新培养及实习生项目”负责。前者以每人300万日元为上限向社会创业者提供“创业支持启动资金”;后者向地方非营利组织派驻实习生,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每月向每人提供10万日元的活动支持资金。
“新公共”支持项目2010年,日本内阁府宣布划拨87.5亿日元预算支持“新公共”项目的发展,各都道府县设置基金,支持社会企业开展活动。同时建立相应组织支持社会企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建设活动开展后台,确保活动的透明性和健全性。例如:建立与组织、人才相关的数据库。官民共同运营委员会负责监督,确保项目的透明、公平和有效实施。
项目的支援服务主要涉及六大方面。第一,信息搜集与提供。项目以推进社会企业各种活动信息的透明性与完整性为目标,开展财务报告讲习会,整合人才、资源等相关信息。第二,捐赠募集活动辅导。项目积极开拓捐赠渠道,派遣专家单独辅导,召开捐赠募集活动说明会等。第三,提高社会企业融资能力。项目就资金利用的问题对社会企业实施重点帮扶,并对融资申请等程序性事项以案例教学的方式邀请专家进行辅导。第四,短期利息补偿。中央及地方政府不仅减免社会企业等主体的委托费,而且对其银行贷款等融资利息进行补贴,减轻援助对象的资金负担。第五,推举公共服务模范。由社区提名,表彰在公共服务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社会企业,在精神方面予以激励。第六,探索解决问题的创新机制。针对地区性问题,各都道府县鼓励当地居民主动参与,与社会企业等组织共同探索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机制,推进民间资源的积累,并为政策发展提供动力。为确保上述工作的透明、公平与效果,在各都道府县还设置了官民共建运营委员会。
普及并提高社会企业的社会认知度
日本经济产业省从2007年9月起,每年召开一次“社会企业研究会”,研究会设立了由社会企业从业者、学者、中间知识机构、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针对日本社会企业的现状、发展和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此外,经济产业省承接的“2010年地区新成长产业创造促进项目”也设立了“社会企业推进研究会”,该会同样由社会企业从业者和有关专家构成,主要探讨社会企业的发展战略及方向。包括2007年社会企业研究会,2008-2009年社会企业促进会议和地区社会企业、区域组织协议会,2010年社会企业网络研讨会及社会企业推进研究会,地区意见交换会等。其次,为提高社会认知程度,2008举办社会企业论坛,2009年开展优秀社会企业选,2010年编制社会企业案例书,2009年与2010年举行社会企业博览会。经济产业省通过社会企业评选活动、社会企业经典案例介绍、制定社会企业统一标识用的LOGO以及举办社会企业全国论坛等方式,大力普及社会企业的社会认知度。
(5)推动社会企业与一般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建立社会企业、地方公共团体与企业等三方合作协作解决地区问题的机制。经济产业省于2010年提出“社会企业互助网”概念。社会企业互助网作为社会企业间的协调者,既能促进社会企业间形成伙伴关系,还能促进个人和法人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多部门的合作、新产业的产生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此外,还能提供技能和知识培训,亦能进行调查和研究,从而为政府支持效率的提高提供重要参考。
(6)力促“社会企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2007年9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牵头组建由专家学者、NPO领导人以及企业界代表等组成的“社会事业(Social Business)研究会”,并邀请其他中央部委的相关负责人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翌年4月,该研究会对外发布《社会事业研究会报告》并提出作为“社区事业”升级版的“社会事业”。与社区事业相同的是,社会事业亦属于采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态。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事业的活动领域不再局限于某个社区或地域,而是可以扩展至全国乃至全球。此外,社会事业的发展程度较高,须兼具社会性(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事业性(采用商业手段并确保财务可持续性)以及创新性(开发新商品或新服务、开发或利用能够制造新商品或新服务的行动框架、通过商业活动创造新型社会价值)三大要素⑬。
2010年2月,经济产业省再次发布《有关社会事业统计及其制度化探讨的调查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事业是指采用商业手段以应对环境和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事业活动体”,同时披露其组织形态包括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⑭。紧接着,为了推动社会事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推动社会事业市场的成长,经济产业省于2010年10月重组“社会事业推进研究会”并于翌年3月发布《社会事业推进会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经济产业省对社会事业的概念进行完善,提出“社会事业是指将各种社会问题视为潜在市场并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使命的事业体”⑮。
规范监管
根据日本内阁府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企业具体要素包括:企业利润主要用于再投资,股东的利润分配低于全部利润的50%;事业性收入占组织整体收入的50%以上;事业性收入中来自公共保险(医疗或护理保险等)的收入低于50%;来自政府依托事业的收入低于50%等⑯。
2005年修订《公司法》,允许股份制公司通过章程部分限制股东所享有的利润分配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从而推动“非营利型股份制公司”的诞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法律甚至允许一般社团法人将利润或剩余财产分配给包括亲属在内的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同时允许一般法人通过成员大会或评议员会的决议,将组织的剩余财产分配给组织成员或组织设立者,从而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于“非营利”概念的认知。
--------------------------------------------------------------------------------
①金仁仙. 日本社会企业发展战略及其借鉴意义[J]. 企业管理,2015,(03):113-116.
② Kerlin,J.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0n, 2010, 21(2).
③服部篤子・武藤清・渋澤健『ソーシャル・イノベーション』日本経済評論社, 2010年.
④俞祖成.日本NPO法人制度的最新改革及启示[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06):116-120.
⑤俞祖成.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制建设与改革动向[J]. 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6,(07):40-45.
⑥藤井敦史「日本における社会的企業概念の受容と研究の課題」原田晃樹・藤井敦史・松井真理子『NPO再構築への道』勁草書房, 2010年。
⑦「コミュニティ・ビジネス」経済産業省HP, URL: http://www.meti.go.jp/, 2017年1月20日最終アクセス。
⑧米澤旦「ハイブリッド組織としての社会的企業・再考」『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662号, 2013年。
⑨山中馨.「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55選」に見る日本の社会企業家の力[ J/OL].創価経営論集,2012,http://libir.soka.ac.jp/dspace/bitstream/10911/3739/1/P.1-12-36.pdf.
⑩山中馨.「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55選」に見る日本の社会企業家の力[ J/OL].創価経営論集,2012,http://libir.soka.ac.jp/dspace/bitstream/10911/3739/1/P.1-12-36.pdf.
⑪俞祖成.日本社会企业政策的概况及启示[N]. 中国社会报,2015-11-23(007).
⑫ 俞祖成:《日本社会企业政策的概况及启示》,载《社会建设研究参考》2015年第16期。
⑬日本経済産業省「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研究会報告書」(2008年4月)。
⑭日本経済産業省「平成21年度地域経済産業活性化対策調査(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の統計と制度的検討のための調査事業)報告書」(2010年2月)。
⑮日本経済産業省「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推進研究会報告書」(2011年3月)。
⑯金仁仙. 日本社会企业的发展及其经验借鉴[J]. 上海经济研究,2016,(06):28-35.
参考文献
Droit, L. S. P. d. l. D. d. (2014). LOI n° 2014-856 du 31 juillet 2014 relative à l'é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 (1)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jsessionid=F3F6FC032F2EDD797976AF8D2CC33491.tpdjo15v_2?cidTexte=JORFTEXT000029313296&categorieLien=id
Medhurst, J., Wilkinson, C., Henry, N., & Wihlborg, M. (2014). A map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their eco-systems in Europe. Country report: France: ICF Consulting Services.
Mendell, M., B. Enjolras, & Noya, A. L'économie sociale au service de l'inclusion au niveau local : Rapport sur deux régions de France : Alsace et Provence – Alpes – Côte d'Azur: OECD Publishing.
Spear, R. (2013). Social economy—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oday’s challenges.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pear, R., & Bidet, E. (2005). Social enterprise for work integration in 12 european countrie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76(2), 195-231. doi:10.1111/j.1370-4788.2005.00276.x